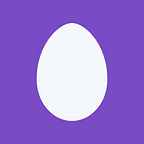四川的地方主义诉求与“联邦主义”的前世今生
“大一统”作为话题最近获得了很多的关注,具体来说,过于集中的中央权力开始受到了质疑和批评,而地方自治带来地方活力和繁荣的设想也开始被更多人接受。“联邦主义”因此作为其中一个替代中国共产党极权统治的方案,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很多人认为一个中华联邦既可以避免共产党崩溃时产生的剧烈动荡,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地方自治。虽然这种立场在今天的中文舆论场中还显得比较新鲜,但在历史上其实不乏先例。“联邦主义”是上述诉求在今天的体现,受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很明显。然而自从蒙元以来,每当中华帝国遇到危机,跟今天的“联邦主义”要求类似的,去中心化,拓展地方自治权利的声音就会出现,如明末的顾炎武和黄宗羲,清末的章太炎梁启超和以宋育仁为代表的四川士绅,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把这种诉求统称为“联邦主义”诉求,也在此去掉引号。四川是联邦主义的重镇,从清末开始便是如此。笔者将会在接下来的篇幅里,用四川作为例子详细阐述联邦主义与四川的地方主义诉求的关系。这里多提一句,用四川作为例子不仅是因为笔者对四川的材料最为熟悉,还是因为四川从各项指标来看,都是东亚各地中等偏上的水平,特别适合作为范本来观察。
从晚清来看,今文经学的一个中心其实在四川,以今文经学为依托的四川的经学兴起得比较晚,成就却非常大,主要是因为四川社会的元气恢复到了较高的水平,地主,绅士,商人都有了相当大的产业和关系网络,张之洞兴蜀学,使得他们看到了阶级巩固和升迁的机会,因此蜀学一下子爆发式的发展。这样的突然爆发,很适合从义理入手的今文,而不适合从训诂入手的古文。清末最有名的今文学家是康有为,但康有为很明显是直接受到四川今文经学,尤其是廖平本人的重大影响。四川的今文家在开眼看世界以后,也像章太炎一样得出了复封建的结论,认为只有恢复西周的封建体制,才能解决清帝国的所有问题。然而跟古文经熏陶出来的章太炎不一样,他们认为要解决封建导致中国分裂的问题,是要把孔教立为国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这个观点其实不是康有为独有的,相反,是当时的今文学家在受到基督教的强烈刺激以后设想出来的方案。四川的今文学家,或者更笼统一点说,儒化士绅们,和康有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乡土性很强,他们的各种方案都是着眼于如何以动静最小的方式,扩大四川的自治权。因此康有为对封建并不感冒,而四川士绅却对此情有独钟。
除了类似于“皈依者狂热”的崇拜孔子和圣人之教以外,四川士绅还有第二点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绅士,即他们跟清德宗建立起了私人联系。宋育仁的光绪三大礼赋为他赢得了朝野的赞誉,骆成骧的“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为他和四川赢得了唯一一个状元的头衔,然而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杨锐跟德宗的关系。四川各界对戊戌变法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认为这是拓展四川自治权的好时机。清末四川人口激增,绅士权力增长,并开始挤压地方官僚的位置,再加上西化的压力,“维新”被广泛认为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工业化可以开利源,解决人口压力。政治改革可以把绅士的权力合法化,西化可以把四川再次和世界联系起来,因此各方各界都积极支持变法。戊戌变法的主力,其实是四川人。除了清德宗以外,军机四章京中有两人是四川人,而杨锐是最受德宗信任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衣带诏给的是杨锐,而不是自己谣传的康有为。杨锐老成持重,认为谭嗣同和康梁走得太近,要求的变法过于急迫,只怕会适得其反(“言论诡而激,不速去,且酿祸”)。结果果然如他所料,他和同乡刘光第血祭变法。而在四川配合变法的士绅,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被寄予厚望的变法遭到如此粗暴的镇压,部分不服气的士绅因而选择了革命党的路线。比如巴县的梅际郇本来是立宪派,后来变成了同盟会重庆支部的骨干。又或者保路运动的领袖胡骏,明知道他在北京的蜀学会场地拿来给川籍革命党人策划暗杀用,却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不能理解戊戌变法对四川士绅有多重要,镇压变法的伤痕有多深,就无法理解四川士绅在20世纪初期的巨变,和为什么革命党人里有这么多四川人。我们可以从各派对杨锐的挽联中一瞥这种联系:
千秋盛业,百日维新,公自大名垂宇宙
法泽长存,音容宛在,我来含泪吊英贤
丹心报国死何辞,恨未血溅帝衣,明臣非罪
青史垂名期不朽,果能书忠董笔,做鬼亦雄
浩浩昊天,蜀道鹃声凝血泪
哀哀孝子,燕山风树有儿啼
戊戌变法给了在清帝国下追求封建复辟的四川士绅沉重的打击。他们对清德宗的忠诚不足以转移到大清国身上。毋宁说,正是因为他们对清德宗的忠诚,让他们无法忍受后权的猖狂。孝钦后是清帝国中后期最大的宪法破坏者,如果儒生对她的评判还有些偏颇的话,她对大清皇帝继承权的肆意玩弄就不只是儒生的一家之言了。成都的翻译进士广安,早在更著名的吴可读尸谏以前,就警告过立载字辈不立溥字辈的宪法危机。这个恶果一直持续到清帝国崩溃,即使在隆裕太后死后,可怜的逊帝小朝廷仍然要经历四大太妃的争权夺利。因此旗人在清末传出来的孝钦与孝定是叶赫那拉的诅咒的坊间神话,很像是对她们的无奈反抗。对四川来说,德宗一死,他们再留恋清帝国的成分就更少了。如果戊戌变法是士绅跟帝国的斗争,那么保路运动就是全川跟帝国的斗争了。顺便说一句,四川士绅在保路期间抗议的时候,举的仍然是德宗的牌位,因为川路商办是德宗在位期间批准的。
四川在清末的大势,立宪与革命基本持平。保路运动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了不完整的民族建构运动,这个笔者在别处已经提过多次,而且整个课题值得单独一篇文章来解释,因此不在这里展开。需要提及的是,保路运动是四川独立初期各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尹昌衡斩杀赵尔丰,夏之时抓捕田征葵,是蓉渝两个军政府可以建立的基础。四川人实际上是在仓促之中,发现了要维持地方自治,只有不得不独立的道理。也正是因为如此,四川在整合各种势力维持自治的时候,总是显得比其他还没有过整合经验的地区要好很多,但比早在清帝国崩溃以前就开始整合的云南湖南和广东等地又要慢半拍。包括四川在内的东亚各地丧失自治的历史,各位已经非常熟悉了。在国共格式化东亚的过程中,四川又阴差阳错的处于中间偏上的位置。在1950年以前,四川社会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很小。共产党最大的破坏集中在50年代到70年代初这20年的时间,通过土改,消灭地方残余武装,饥荒和文革武斗的方式残杀了超过千万四川人,犯下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罪行。在共产党的极权体制从70年代中期在四川逐渐瓦解以后,民间社会又开始成长,并与正在消退的共产党势力进行拉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失去苏联的支持以后,很像是土木堡之变以后的明帝国。在它无力持续维持中央政府集权的时候,不得不释放出分权的信号,也许以“分税制”的名义,也许以“市场经济改革”的名义。在这个过程中,元气稍有恢复的四川又再一次成为了支持联邦主义的重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怡。王怡在《地方主义与四川》和《宪政与联邦主义》当中,已经比较清晰的展现出了他的想法。他最难能可贵的一点,不在于倡导联邦主义,而在于他试图为“四川”寻找一个新的,可以凝聚认同的符号,“道家气质”:
前段四川人物周刊有一个摄影记者过来,说你们四川人的电梯要比我们上海慢,到了门还老是不开,是不是你们故意调成那个样子的,让我着急死了。我前段时间 看到台湾有一个记者,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不可思议的成都人,成都人起的最晚,最喜欢睡懒觉,走路最慢。钱很少,活的也很滋润,这里面有逍遥的理想,这个逍遥的理想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四川是活在儒家文化圈的边缘,四川的知识份子,从历史上一路数下来,四川的文化人,四川有很多了不起的文化人,但是 四川基本上不出圣人,山东出圣人,最大的圣人和最大的盗贼都出在山东。但四川的文化人基本都是怪才、鬼才,异端。都像李白、苏东坡这样的,都是要打倒孔家店,要写厚黑学的。这是中国传统道家的精神,对苏东坡来讲,东坡肘子是最重要的,立功立言立德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四川文化人的特点,就是求逍遥求自在。
逍遥就是无所待,大鹏展翅,但没有大风就飞不了, 还是有所依赖,四川传统的文化品格所追求的逍遥就是这样,我不跟你合作,但是我也看不到人与人之间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所以庄子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也看不到两条鱼,三条鱼怎样在一起创造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当中的自由生活,他看不到,所以这是逍遥。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所以四川人的精神状态,最重要的文化品格,我认为是后逍遥,前自由的状态。我们没有看到出路,但是四川人的文化品格在传统来讲还是非常了不起的,前逍遥后自由的状态,很大的消解了中央集权的文化的向心力,对人的精神的压迫力消解了,消解了传统儒家礼仪对人性的束缚…传统的儒家礼教对人性的捆绑,在四川是最低的。所以生活中也有很多的人讲四川女性的地位是很高的,四川的男人做饭是做得最好的,生活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也不是给四川的男人做广告…
…所以这是四川文化的品格,道家的气质。道家的气质是求逍遥求不到,求自由也求不到。所以我们说四川是整个中国出怪人最多的人,以前的传统民间宗教是称为所谓的“反动会道门”,49年取消了,50年刘伯承进了四川之后,狠狠的把四川的会道门镇压下去了,因为在49年以前的传统社会,四川的会道门是最厉害的,我以前找到一个会道门的资料全编,我看到49年以前中国的各种会道门的组织几乎有一半的总部在四川,或者发源在四川,或者会首在四川。所以刘伯承进到四川之后,四川镇压会道门非常的惨,也是最厉害的,最血腥的。杀了几十万四川人…
…这几十年也是,尤其是我老家,我老家是绵阳,整个川北是最出怪人的,我举几个例子,海灯法师,严新气功师,在我们老家的山上修炼了好几年。我们老家旁边的山很有名,胡万林也在那座 山上修炼过。一千多年前李白在那个山上也修炼了好几年,跟着道士学剑。刚才我也提到,在49年以前,有一个人李长之写过李白传,他基本把李白描绘成道家人物,对李白学道的经历,包括道家的气质,逍遥的气质。49年之后,他又重写了李白传,李白就变成爱国主义诗人了,把道家的气质就去掉了,四川的道家气质, 特别出这种怪力乱神的人…
…也包括像牟其中这种人,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的人,这也是道家带来的影响。我们不是说道家气质,意味着四川人很了不起,道家气质也有负面的。就是他找不到出路。我们回过头来说蒲殿俊,他是真的很了不起。因为四川是整个中国凹下去的一块,我们都知道,以前有本书叫天下四川人,就是四川移民的状况,四川两千年的历史,我叫做被进入的历史,因为四川的两千年的政治史就是被进入的历史,最早是秦孝公入川,我们给你们送一条金牛,所以四川就把路修好了,结果人家的军队就进来了,所以成都现在就有一个金牛区,这是古蜀国的亡国。今天我们也看到像其他的考古,我们发现四川远古的文化和中原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发源,虽然我们说它在儒家中国的边缘,但是最终还是纳入到了儒家文化的版图里面,我们可以数一数。不管是秦孝公入川、还是诸葛亮入川、满清人入川,蒙古人入川,还是国民党入川、共产党入川,每一次来了就杀人。四川人两千年的历史不是四川人自己的历史。四川人对你来讲是什么概念?我刚才讲是客体,在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当中,四川是一个客体,我们说地方永不被发现,49年以前,整个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理解是地方主义的兴起,最早在檀香山最早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宗旨里面写的是要建立合众国,就是联邦共和,到辛亥革命之后,武昌起义之后,18个省宣布独立,在宣布独立的通电里面,提出的政治理想都是联邦共和。在整个30年间就是联邦共和的理想,让地方重新成为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联省自治,20年代到30 年代,四川和广东、湖南,这场运动中的三个重镇,湖南是闹的最厉害的,早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梁启超就给陈宝箴写信,建议湖南自治。说如果天下的局势都败坏不可收拾,中国可以联省自治,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国家,当时就这样的提出。四川在政治上主要是一个被进入的地方,譬如湖南是一个输出革命的地方。不同的省有 不同的文化品格。到了20年代联省自治的运动当中,湖南是全国第一个颁布出湖南省宪法的地方,当时的省宪制度。四川比较晚,但是四川没有成功,所有的川军将领发布了一个四川自治公约,因为北洋政府不断的抑制,国家政府很腐败。四川人就站出来自治,这也是北洋政府感到最头痛的…”
然而他却令人遗憾得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49年以后,我们进入了完全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再也没有地方了。改革20年来,个人开始觉醒,地方也开始觉醒,我把地方的崛起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分公司的阶段,省的意思就是分公司,分公司和总公司之间的关系,分公司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你只是一个派出机构,最近20年的市场改革,带来了地方的鼎盛,地方在财富上的鼎盛,在文化上也逐步鼎盛,在政治上也开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了,四川省政府在某些事情上也会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了,比如90年代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制度的时候,98年大洪水以后要求四川省退耕还林的时候,地方政府也会要价。这个时候就慢慢过渡到第二个阶段。
就是子公司的阶段,子公司就有独立的人格了,中国若是一个集团,每一个省,甚至每一个省里面的每一个市就是子公司,由中央来控股的独立的法人,中央仍然是控股股东,我们今天实际上就处在这样的阶段,所以中央在某些问题上,在我们这个社会地方开始被迫的承认地方的存在了。94年分税制改革,中央必须坐下来和地方谈这个问题,中央越来越穷,地方越来越富,就谈分税制,谈国税和地税分开,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像以前中央集权那样完全的垂直,而是开始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划分。
《南方人物周刊》做这个专题,也是在文化上去重新发现一个地方,重新构建一个地方。第三个阶段仍然是子公司和公司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反过来,不是中央控股,而是地方去控股中央,什么叫议会,议会就是这个国家的股东大会,就是由各个地方控股中央,让我们的权利从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在英国的法律谚语有一句话“国家的权力到我的鼻尖为止”,这是个人主义的起点,进而去发现一个地方,让它成为不再遥远的地方,而是成为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地方,我们的权利从这个地方往下延伸,包括我们文化上的品格,我们的情感都从这个地方去延伸。这个国家才有真正的希望。这是我所理解的地方主义和四川的关系。“四川”这两个字,“地方”这两个字在我心中的意义。我们要建设新的四川,我们才有新的中国。
王怡牧师是一个很有勇气也很有思想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在实践自己的理想。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才让人感到遗憾,因为笔者认为联邦主义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
联邦主义是蒙元式大一统在无法维持自身时的补救机制,用更通俗一点的话说,是它的韬光养晦政策。它希望暂缓大一统的进程,给予宋儒式乡治足够的成长时间,等到宋儒社会成长到足够强大以后,再次恢复大一统的伟业。然而这样的计划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当大一统帝国放弃中央集权,推进地方自治的时候,如何避免藩镇化甚至解体?清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如何判断什么时候地方自治成长到足够的时间,可以再次集权了?明帝国一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联邦主义只能是苟且之治,迎合人们虽然不愿意放弃帝国野心,但又希望逃离暴政的矛盾心态。从现实上来说,联邦主义是一种中间状态,天然不稳定,要么导向藩镇化和解体,要么导向仓促集权而崩溃。为了更详细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联邦主义的前世今生:
从上层设计来说,蒙元大一统为学术界所谓的“晚期中华帝国”,即明清,提供了统治范式。“大元”不以开国帝王的龙兴之地为国号,而以开启新时代为国号,彰显了它建立多元大一统制度的庞大野心。然而正如前田直典和大部分蒙元史学者指出的那样,蒙元帝国的统治形式,主要是试图复制它在蒙古的模式,部分而不是全盘吸纳震旦的模式。对后世影响深刻的行省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行省是一个一个的军事征服区,然而蒙元帝国并没有打算用科举产生的官僚来管理这些地区,因此各个行省长官的权力异常强大。而蒙元帝国无法直接征服的地区,或者蒙元帝国征服时的合作者,就是土司领地。行省和土司制度,是蒙元帝国留给后世最大的遗产,他们是维持“多元大一统”的必须。然而蒙元帝国作为这种新的大一统模式的开拓者,并没有足够的治理经验,缺少科举官僚体系的支持,就无法产生有效的财政体系,使得地方长官,豪杰,邪教等势力各找生路,最终撕裂了蒙元帝国。明太祖所谓“元以宽失天下”,其实就是说蒙元的管理制度非常混乱(或者说多元),没有井井有条的中央行政来维持帝国的存在。
从基层实力来说,新儒家(neo confucianism)吸收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貌似完善了自己的理论建构,其实留下了非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但他们驯化了扬子江以南的“生番”,重新定义了基层共同体。我们要注意,这里并不是说基层共同体就只有新儒家的宗族,而是说,他们获得了社会主流的强势地位和定义其他共同体的权力。宗族和由宗族产生的士大夫,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征服者的合作者。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皇帝垄断武功,他们垄断文治。当这个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他们也会在有需要的时候拿起武器,这是“熟番”还残留的武力,或者扶持其他有武力的团体。然而不管是文还是武,依靠宗族的新儒家共同体都无法支持起蒙元帝国设想的那种大一统模式,因为他们一离不开科举制度的支持,二无法将社会覆盖范围拓展到外姓和乡县以外。大一统的野心与基层社会的脆弱形成了鲜明对比,滋生了盐帮(张士诚),哥老会,“邪教”(红巾军,白莲教,太平军)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宗教团体。他们与帝国和儒家宗族的三角博弈(在有些地区还要加上土司领地的四角博弈),是元明清社会史的主旋律。
洪武来自摩尼教,最后不得不利用儒家士大夫才能整合蒙元帝国在东亚的版图。他鉴于“元以宽失天下”,因而济之以猛,大行集权之术,消灭蒙古残留势力,改土归流,在最初的集权效果结束以后,明帝国陷入了及其不稳定的局面,“与民休息”与“苛捐杂税”交替出现,不过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如果小冰川时期(Little Ice Age)对帝国的命运真的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是体现了明帝国自身的脆弱。在蒙元的“宽”和明的“猛”都实验过以后,顾炎武和黄宗羲其实想要的,就是在这之间找到平衡,也就是今天所谓联邦主义的雏形: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这是顾炎武著名的《郡县论一》,或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论方镇:
今封建之事遠矣,因時乘勢,則方鎮可復也。自唐以方鎮亡天下,庸人狃之,遂為厲階。然原其本末則不然。當太宗分置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帶甲十萬,力足以控制寇亂。故安祿山、朱泚皆憑方鎮而起,乃制亂者亦藉方鎮。其後析為數十,勢弱兵單,方鎮之兵不足相制,黃巢、朱溫遂決裂而無忌。然則唐之所以亡,由方鎮之弱,非由方鎮之強也。是故封建之弊,強弱吞併,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埸之害苦無已時。欲去兩者之弊,使其並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乎…統帥專一,獨任其咎,則思慮自周,戰守自固,以各為長子孫之計…
其中“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和“是故封建之弊,強弱吞併,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埸之害苦無已時。欲去兩者之弊,使其並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乎”其实都是在试图维持明面上的大一统的同时,给基层共同体喘息和修养的时间。但是这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天子政教如何能普及到方振或者封建领地,使得他们不分裂呢?到底要把权力集中到什么地步,才能避免郡县之弊呢?这两个问题还没等到解决,清帝国就入关了。事实上,等到顾炎武和黄宗羲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反思的时候,清帝国已经入关好多年了。清帝国从一开始,操作士大夫和官僚机器的手段就比蒙元高明的多,但也正因为如此,清帝国统治集团自身受官僚国家的影响也深得多,除了外蒙古和西藏还保留了许多实质上的自治和特权以外,满洲和内蒙古的基层社会被帝国侵蚀和破坏得严重得多。清帝国击败准噶尔是一场惨胜,对帝国的生死存亡,比灭三藩危险得多,因此才会心有余悸的对准噶尔进行灭族。外患暂时平定,而在帝国内部,当征服者失去了武力垄断,而士大夫失去了文治垄断的时候,新的文治武功结合体,比如白莲教和太平天国,就要开始登上舞台了。大一统的理想和基层的脆弱之间的鸿沟再一次无法弥合,眼看就要重复蒙元和明帝国的结局,结果西方势力的介入,为这个游戏加入了新的因素,因此让清帝国变得更蒙元和明有了很多的差别,也因此孕育出了新的可能性。
清末的联邦主义因此值得好好的探讨,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后太平天国的政治格局,从清末新政开始,经过辛亥革命和民初的国会政治,然后通过20年代的联省自治,直到共产党击败国民党的前夜,都还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清末的联邦主义主要是受到经日本过滤的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影响,然而却很有意思的,按照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分成了两派。今文经学这派,已在上文详述。古文经学这派,我们比较熟悉,以章太炎为代表。他借用当时流行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跟古文经学融合,推导出炎帝黄帝为“汉族”的祖先,主张联合日本而排挤满洲,要废掉王权而建立小的“中华民国”,因此从理论上解决了顾炎武和黄宗羲的联邦主义解决不了的问题,即天子政教如何感化封建诸侯,不要让他们分裂的问题。章太炎的意思是,既然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那么如果没有外族的影响,抛弃了满蒙藏等非汉地,我们应该自然而然可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需要考虑分裂的问题,这样既维持了小的统一,又保证了地方自治。这个“汉族”的问题已经被批判得非常多了,不需要笔者再赘述了。章太炎最后也看到了自己所设计的小中华民国被盗窃的命运,可谓求仁得仁。梁启超虽然本人影响比章太炎大,但对联邦主义的重要性却比章太炎小得多。梁任公的特点就是杂而不精,喜欢新潮理论,经常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他的联邦主义观点是当时流行思想的堆砌,虽然和康有为/孙文的集权诉求有明显的差别,却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突破,即还是无法回答集权和分权的平衡点问题。清帝国倒台以后,联邦主义脱离了理论范畴,正式进入了实验阶段。袁世凯错误的以为美国人古德诺设计的君主立宪和他自己的“汉人”身份可以完成天子政教对封建列国(民国各省)的整合,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北方各省仍然为了北京城大打出手,南方各省情况不一,湖北,江苏,浙江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北方,湖南,四川,广东,云南则早就想自立了。因此民国其实有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出现,“联省自治”的提出,其实是联邦主义已经快要结束的,而各省独立,尤其上述南方各省的独立快要来临的时候了。国共以猛济宽,消灭了地方自治,联邦主义正式结束。
这是目前主流的关于联邦主义认识的线索。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会提到47行宪和张君劢设计的联邦制,但笔者认为那是只是旧民国的回光返照,而不能算是联邦主义的尝试了,因此就不做讨论。在这个主流线索里,我们可以看到从理论设计和实际操作两方面,都存在我在本文开头时提到的联邦主义的核心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联邦主义会出现这种不稳定状态:
第一是因为东亚各区域的情况本来差别就很大,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很难整合起来,举个例子:蒙元明清三帝国,浙江,福建和广东的沿海一带本来是跟日本和东南亚贸易交流非常多的地方,而山西陕西则跟内亚的贸易交往更加频繁。如果强行糅合成一个政体,用行政权力打断更自然的贸易连接,那么会出现的就是明帝国的海禁问题和清帝国的晋商挤压粤商的问题。各地不平衡的压力最终会撕裂国家,导致解体。
第二是因为省界与具备邦国条件的共同体不重合。同一个省里,很可能有互相敌对的势力(江苏)。同一个长期形成的自然历史边界里,可能被划成了两个甚至三个省(汉中归陕西)。因此等到基层共同体如人们所愿开始成长的时候,他们和省界往往有很大的差距。比如其实主要是集中在合肥一带的淮军,以奉天为核心的奉系,在蓉的四川军政府和在渝的蜀军政府对立等。因此各省下面的实力人物在能够代表本省说话以前,都必须先要统一本省的各种势力。在山西,云南,湖南和广东,这个过程相对短一些,在四川花的时间就要久一点,而在湖北,江苏,河南河北等地,这个过程甚至一直没能完成。长期的中华帝国统治导致的许多乡县凋敝,基层发展情况参差不齐,因此又加剧了上述的各地差距,使得联邦更难以维持。以民国为例,因为各地的本土性差别太大,导致自治起来效果千差万别。湖北本来是天下第一强的鄂军的发源地,却因为成名太早,引起袁世凯猜忌,受到打压,很早就丧失了自治,受北京的压制。而从19世纪中叶以来,川盐和海盐交替冲击汉口市场,让湖北省摇摆于上江,下江和中原之间。湖北当地势力想要打倒外地人王占元,就会想要引入本土性更好一点,又跟湖北有紧密的经济联系的四川势力,来赶走帝国性更强的下江势力和中原势力。这样一来,帝国势力和本土势力在联邦内部开战,实际上已经让联邦无法维持了。
第三是东亚各地并没有天然的共主可以作为解决上述各种不同的最后依靠,再直白一点说,就是没有合法统治者可以涵盖整个东亚大陆。这个的讨论已经非常多,就不需要在这里多说了,只补充一点,引进西方的统治符号并没有解决这一点。
然而联邦主义的尝试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第一,它向我们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即根据东亚近一千年的情况来看,要求地方自治,就必须让要求自治的各团体独立,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第二,它向我们证明了,即便或者正因为中央权力最膨胀,集权最深的时候,要求脱离集权的暴政和地方自治的声音总会冒出来。而在这些声音当中,巴蜀的声音永远是最响亮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