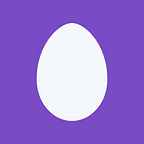成都血战:巴蜀的1989
前言
在我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巴蜀利亚协会的工作以后,已经很少再有机会写文章了。除了工作重心转移以外,我认为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剩下的 — — 就像倭文端公说的那样,如果你真的相信程朱的道理 — — 只是去执行而已,然而最近的一些事情让我又重新燃起了写作的兴趣,主要的刺激来自于沦陷区的白纸革命。在习近平的高压统治之下,参与或者同情白纸革命的人,他们的政治启蒙方式跟我这一代人(80末90初)可能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代人的政治启蒙,是东亚80年代末的民主化运动(普遍被称为“六四”)的直接结果。这波民主化运动的失败与后果直接刺激了我们的父辈和我们,比如我们这一辈大多数人是直接从我们的父辈那里听到的“六四”。而白纸运动这代人的政治刺激的来源却很有可能来自网络,已经有很多人说过他们是从网上知道“六四”这件事的。视角的不同会很容易的让两代人心中的“六四”完全不一样,我们认为是很清晰明了的前因后果,我们脑子里的“好人”和“坏人”,很可能跟他们对“六四”的想象有千差万别。而由于不管是中国官方的讳莫如深,还是海外民运的支离破碎,都无法提供关于“六四”的一个系统的叙事体系,因此所有人都只能模模糊糊的用“民主”,“自由”,“抗争”这样的符号来郢书燕说,互相之间其实根本没有实质性的交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以我的视角,特别是以区域和地方为主要视角,来重构“六四”。熟悉我的朋友大概能看出,我这个初衷和当时写的那篇拙作《“六四”,成都与巴蜀》的初衷一致。然而那篇文章在今天看来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和可以补充的地方,因此本文将试图在当时那篇文章的基础上,以巴蜀本土视角为主,做更详细的阐述。
那么什么叫以巴蜀本土视角为主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成都发生的学生抗议,是在北京屠杀以后才开始的,6月4日之前,成都的抗议声音(相对于北京和其他地方来说)还非常小,直到解放军开始屠杀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的消息传到成都以后,成都的声势才突然增大了起来。而中国以成都为核心的武装对抗抗议群众和学生,基本上是从6月5日开始的。因此,按照巴蜀本土的视角,把这波民主化运动叫成“六四”就非常奇怪。因为它的展开和结束过程,跟北京的抗议有非常大的区别,很难被称作同一个运动。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巴蜀地区在80年代末的民主化抗争与其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巴蜀地区的人民跟红色中国的斗争史的一部分,因为以成都为核心的这次民主化运动,地域特色非常浓厚,它更像是从1950年巴蜀第三次反恐战争(共产党所谓“西南剿匪”)失败以来,一系列区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为了“中国民主”的一次抗争。本文将因此以上述的本土视角,来重构巴蜀地区在80年代末的这次民主化运动。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作,难免生疏,希望各位读者原谅。
领袖群英吾与汝:巴蜀独立时期的得与失
与89年的抗议非常相似,近代巴蜀的独立,乃至清帝国的解体,也来源于成都的一次抗议,此即1911年5月9日的“成都血案”。巴蜀绅民自行出资修建的川汉铁路,被清帝国粗暴收回,士绅领袖们因为抗议而遭到清帝国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抓捕,人民愤怒的要求释放被捕领袖,却遭到赵尔丰的血腥镇压,这就是“成都血案”。血案一出,巴蜀各地民兵武装纷纷起义,重庆军政府领袖夏之时斩杀指挥开枪的田征葵,成都军政府领袖尹昌衡斩杀赵尔丰,为牺牲的示威群众报仇,紧接着成渝军政府和平合并,巴蜀地区实现独立,清帝国也随之瓦解。巴蜀独立后,巴蜀地区的人民迎来了自宋明帝国的残酷统治以来,最繁荣,最自由,最有活力的历史阶段。本段的“领袖群英吾与汝”,来自于四川高等学堂的校歌:
岷山峨峨开天府,江水泱泱流今古。
聚精会神生大禹,近揆文教远奋武。
桓桓熊罴起西土,锵锵文教适东鲁。
祭神人,歌且舞,领袖群英吾与汝。
这首校歌不仅反映了巴蜀人开始有意识的将巴蜀地区视为一个整体,而且流露出了强烈的自我治理的愿望。因此,从获得独立的1911年开始的20多年间,自治成了所有巴蜀人的共识。这样的共识让他们勇于面对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共产党曾经两度大举入侵巴蜀,一次是1920年代的渗透和颠覆,一次是1930年代红军的直接入侵。这两次入侵的企图都被巴蜀军民以极大的代价挫败了。然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民族构建的浪潮从西方传入东亚,给“自治”加上了一个前提条件,即只有具有民族国家机器的共同体才能维持自治。独立时期的巴蜀人没有及时构建出不同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或者汉人的“巴蜀民族”,因此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制,在关键时刻无法将全体巴蜀人动员起来,最终在蒋介石1935年入蜀以后,失去了独立。蒋介石以“中华民族”领袖的身份绑架巴蜀人,以巴蜀为殖民地疯狂掠夺资源,来应付他本人发起的中日战争。战争结束以后,他又抛弃了满目疮痍的巴蜀大地,逃亡台湾。巴蜀军民不得不以疲惫的身躯独自面对由苏联全力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无法抵抗,从1950年开始成为了红色中国的殖民地。
血战到底:红色殖民下的巴蜀
“血战到底”一词曾被广泛的用来描述中日战争期间的巴蜀军团。其实中日战争期间,巴蜀军团的高伤亡率并不源于巴蜀人跟日本人打仗特别卖力,而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将巴蜀军团当作人肉盾牌,并不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的缘故。因此中国将蜀军的高伤亡称作“血战到底”,是天大的讽刺。然而血战到底却可以非常准确的形容巴蜀人在红色殖民下的抵抗。从1950年的第三次反恐战争开始,巴蜀人利用一切机会,反抗红色中国的殖民统治。这其中有两次抵抗的高峰,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巴蜀本土造反派利用局势,将巴蜀大饥荒的主要执行人李井泉从上海抓捕回巴蜀,并同时打击了多地的县委,市委,和四川省委等红色殖民机构。第二次是80年代初,巴蜀各地的民间教团开始复活,反抗的高峰是曾应龙的“大有国”,直接公开反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系列的反抗并不是偶然出现的,贯穿始终的,是巴蜀人对红色殖民不懈的抵抗,不管他们使用的标签是“民团”,“造反派”,还是反对“计划生育”。我们即将看到,80年代末的民主化运动,也并不例外。
80年代巴蜀民主化运动的社会基础:
巴蜀地区是中共最后攻占的地区,又是国民党最后的反攻基地和青年党的发源地,因此跟中共攻占的大部分地方不同,巴蜀本土很难找到符合中共要求的干部。邓小平主政巴蜀期间,不得不从“解放区”大量调集干部入驻,非如此不足以稳定中共在巴蜀的基层统治。即便按照教条的共产主义原则,在巴蜀本地选出来黄廉这样出身贫下中农的干部,也会说出以下这样的话:
我认为中国的前景还是要发扬民主,要让群众讲话才能监督领导,毕竟上级领导不是天天在书记身边。我还说到人事安排上也有问题,在战争年代党叫干啥就干啥是对的,和平时代还是要发挥个人特长,应该让自己选择工作合适的工作岗位,我自己只适合当教师,不适合搞宣传工作。我还说我们的工会工作是虚设,工会最好是民办,官办工会没有作用。(《黄廉访谈录》)
因此,中国必须在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运动,消除独立时期的军绅政权的社会基础的同时,进行更大规模,更彻底的,波及到普通人的社会革命。这首先激起了1950年的第三次反恐战争,紧接着引起了从50年代中开始的,长达十几年的巴蜀大饥荒。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毛泽东在1972年的革命外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美国开绿灯,欧洲和日本为先锋的“四三方案”,率先解开了红色中国的经济死结。大量轻工业和农业技术的输入,缓解了中国统治区的贫困,其中包括巴蜀。巴蜀地区,既不是因为“要吃粮,找紫阳”的赵紫阳,也不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而是结结实实的因为西方化肥的输入,才彻底摆脱了1950年就开始的不同程度的饥荒。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统列宁主义者发现,在文革后维持党国统治一切的政策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在巴蜀的殖民统治模式不得不有所侧重。在维持党对核心部门和关键企业的领导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开始:
1.吸纳在1972年以后缓慢恢复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精英。邓小平乞灵于中华帝国的传统智慧,恢复了当代科举 — — 高考制度。从红色中国/中华帝国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大学生是候补干部,虽然政治并不过硬,但可以承担一些技术工作,尤其是迫切需要与西方接轨的那些技术工作,而最能抓住这个机会的,是巴蜀独立时期残留的乡土精英的后人。他们在红色中国内,依靠残留下来的知识和能力勉强维持生活,在高考开放以后,凭借着家族带来的历史沉淀和自身的努力,考入了大学,并接受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资源,因此想利用红色中国的体制来做出改变。
2.在高考制度以外,在党国体制不能完全覆盖的灰色地带,允许“个体户”和其他私有制模式的出现。最早的个体户和各种私有经济的探索者,多是政治运动时期被挤到边缘的人物。其中有土改期间被划分成地主和富农的人和他们的后代,有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造反派”,还有一些是单纯不满红色殖民的普通人。他们有许多先是利用文革,打击了驻扎在巴蜀的红色殖民政府,文革结束以后,有些人仍然拥有武装和组织,又在80年代初的“严打”期间遭受进一步的冲击,然而他们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被划分成了所谓的“社会渣滓”或者“无业游民”,其中包括黄廉本人。曾经压在他们头顶的天花板突然抬高了,他们瞬间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急需一个名号来保护自己来之不易的生存机会。
这两种人,他们的家庭跟红色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恩怨纠葛。虽然远离统治核心,又觉得应该获得权力,因此急需一个政治上的标签来满足他们重新燃起的政治需求,而“民主”,恰好是他们当时可以使用的最好的标签。正是这两种人,构成了80年代末巴蜀民主化运动的核心力量。
而“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又成了最好的舞台。首先,整个巴蜀地区的大学生精英都往成都聚集,因为成都有“四川省”最好的学校,在文化上又比较契合,不必去外地读书,还需要学习普通话和习惯气候饮食,非常不便。其次,成都平原的个体户和各种私营企业,秘密结社组织等也往省城聚集。第三,成都是巴蜀地区西方人最多的地方,拥有最高的国际曝光度。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让成都成了巴蜀民主化运动的中心。这里需要额外补充一点,这并不是说巴蜀其他地区没有自己的民主化运动,比如重庆和泸州等地就有自己的抗议和游行,但由于材料的限制和敏感资料无法接触的原因,这些地方的民主化运动的历史恐怕只有等到巴蜀恢复独立以后,才能好好挖掘了。
成都:血战三日
成都的民主化运动,一开始就跟北京和中国其余地区有很大差别,最开始的抗议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反官倒这样不痛不痒的口号中,甚至跟“民主”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当地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社会学教授,带我了解了豪华的锦江宾馆的情况。他指着那些独自坐在酒店酒吧喝着橙汁的女人说,这里的消费是普通中国人负担不起的。看起来,这些女人似乎是妓女。我们看着一个年长的男人走到其中一个女人那里,然后两个人走出餐厅,消失在电梯里。他说,那名男子是一名著名的将军,公众知道酒店里发生的这种事情,并将其视为失业严重时期政府腐败的一个主要象征。”(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据我6月5日采访的美国领事馆官员斯科特·贝拉德(Scott Bellard)说,最开始在成都没有真正的学生民主运动,但在年轻工人和失业青年当中存在巨大的动荡,主要是对腐败和失业感到忧虑。”(同上)
“不过他们的诉求有别于北京的学生。‘我印象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它从来不是为支持民主而抗议的。’金鹏程(Paul Goldin)说。这位宾州大学的中国思想教授,昔日是在四川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从他的角度来看,学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体制从里到外变得更纯粹,他们并不想推翻共产党,反而希望党能遵守自己做出的承诺…之后很久,所有人都知道北京建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之后,那时候,人们才开始使用自由、民主这种词”(《人民失忆共和国-成都》林慕莲)
紧接着,成都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出现了:它是在不断的反抗政府的暴政之下,才越来越强大的。换句话说,对中国政府的仇恨,而不是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才是成都运动真正的核心动力:
“五月十六日的清晨是成都抗议行动的转折点。当时超过千名的警察与大约两百名学生扭打成一团,警察在清场过程中动用棍棒和皮带殴打学生…那晚的暴力清场刺激了这场运动…有近几十万人在警方行动之后走上街头,还有多达一千七百名的学生参加绝食抗议。成都变成了游行参与者的聚集点,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其他地区蜂拥而入,甚至有远至西部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代表团来参加抗争。学生们在墙上张贴的海报中写满了他们的希望与渴望,像是‘不自由,毋宁死!’抗议在当时成了家常便饭,在某些圈子里,连日常的问候‘吃饭了没?’都会半开玩笑地变成了‘你抗议了没?’”(《人民失忆共和国》)
四川省曾是赵紫阳的封疆,时任四川省党委书记杨汝岱又是赵紫阳的门生,因此四川党委迫切的想要把成都的运动解释成为支持北京学生的运动:“党委副书记顾金池对学生说:‘我们清楚的知道你们的绝食运动是为了支持北京学生…”(同上)成都的抗议活动确实与北京的学生运动有一些理论上的联系,但两地的社会背景差距太大,产生运动的原因也如上述般各不相同,因此四川省委的举动更像是顺势而动,借机配合赵紫阳和中央党内支持学生的派系,而不是对成都运动一个符合事实的描述。
当然,成都与北京最大的区别和关联,都来自于6月3日当天。当北京的屠杀正在策划和进行的时候,成都的抗议者已经所剩无几。然而当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BBC和VOA传到成都以后,全城才真正的被点燃了。也就是说,北京的抗议结束以后,成都的运动才正式开始:
“在几个小时之内,充满杂音的英国广播国际频道以及美国之音却传来了北京的屠杀消息,于是数千名愤怒的市民又再度回到了成都街头。这次的群众运动展现出坚定的团结与无畏的勇气,街头的抗议者清楚知道军队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火。数千人在成都的主要道路上游行,他们举着哀悼的花环和标语,上头写着‘我们不怕死’、‘六四屠杀,七千人死伤’、‘打倒独裁政府!’当第一波的示威群众游行到武警部队面前时,局势变得一触即发。群众的攻势被警方挡了回来,武警开始用警棍殴打示威者。现场登时爆发为全面战斗,抗议者用鞋子,砖头,人行道上的碎片,以及任何他们能够取得的东西回击武警部队。”(《人民失忆共和国》)
“然而,成都人并没有被政府撑腰的暴力镇压给吓唬住。相反的,他们被激怒,变得更加义愤填膺…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没怎么伪装的警察。‘愤怒的群众立刻揪住了他,像成群的老鹰一般扑向他,在我们眼前血腥地将他踩死。这种严厉的私刑让我深深震撼,它血淋淋地显示了人民对警察有多么反感。’”(同上)
至此,长达三日的血腥巷战在成都市民与中国警察之间展开。尽管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多有出入,而且各方的描述区别甚大,但是有一点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那就是从6月4日下午开始,到6月6日晚,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都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政府及其代理人。不管是市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还是国有企业,都成了成都市民的攻击对象。他们忠实的履行了“打倒独裁政府”,“暴君人民绝不放过你”,“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承诺,在实力对比明显不利于自身的情况下,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巴蜀人反抗中国统治的悲歌:
“到了六月四日傍晚,一群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任何属于公家的物品,包含公共汽车和警车。群众向广场附近一个殴打拘留者的警察局投掷石块,瓷砖和汽油瓶,最后还引爆火势。大火蔓延到早被洗劫一空的‘人民商场’ — — 一个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的国有市场…六月五日早上,成都的市民一觉醒来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街上有很多焦黑冒烟的公车,现场出奇的安静。而且唯独国家的财产遭受攻击,政府大楼的每一块玻璃都被打碎,而旁边的私人企业则毫发无伤…政府当局好像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一份解密的美国电报指出,武警部队的人数远远不及民众人数,他们为确保自己的安全,被迫撤退到市政府大楼。每一次武装部队试图出击的时候,都因惊人的群众数量而迅速撤退,最多只能偶尔向人群投掷几颗烟雾弹。”(《人民失忆共和国》)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将巴蜀的抗议称为“六五”,而不是“六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成都抗暴过程中,最有象征性的冲击政府大楼,和市民与警察最激烈的战斗,都发生在六月五日:
“6月5日上午12:15,我写了如下:
“街上到处都是人,一片混乱。”
“当我沿着人民南路走向广场时,我开始见到倾倒的垃圾桶和路边的栏杆。距离毛泽东塑像一个街区的地方,年轻人正在建造一个简陋的路障。最终,我壮起胆子从广场中心穿过,满地都是碎玻璃和垃圾。
“看不见有警察,但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扬声器播放公告,一个声音说到:“我们五分钟后就来抓你。”又一阵恐慌爆发了,人们都纷纷逃走。”
“大约午夜12:15分的时候,我在广场往右转,看见路上有燃烧的物体。两辆城市大巴,也许就是下午5点左右我看到的警察拖过广场作为路障的那两辆大巴,烧的只剩车架了,轮胎仍在燃烧。再远一点,一辆三轮警用摩托车也在燃烧,然后我意识到我正在走过的街区有一半着火了。”
“年轻人打烂窗户、摧毁建筑物,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成都体育大学的一位没有参与抢劫的学生告诉我:‘人们正在燃烧建筑物,因为政府不好。戒严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喜欢它。’”
“三辆消防车从广场的方向开过来去扑灭熊熊大火。但当他们停下来,连接水管并对准火焰时,人们包围了消防车,并在五分钟之内将其中一辆点燃,并将另一辆翻过来!难以置信。人群吼叫着表示赞同。五分钟后,催泪瓦斯罐头开始爆炸,人们逃离,这种恐慌情绪并未停止,因为爆炸不断发生并且越来越靠近 — — 四,五,六个。”
我接着写道:“这是一个有趣的教训。从当局角度看,这展示了事情如何‘失控’,甚至可以‘证明’他们的论点,即骚乱是‘少数暴徒’或‘几撮不良分子’造成的。当局对于和平示威出重拳,激怒了他们。在开始实行强硬路线后,他们无法退缩,只能严厉打击。愤怒的人们,开始抢劫、放火。当局不能让建筑物就这么被烧毁,所以他们派出消防车。当人们把这些都点燃后,催泪瓦斯就来了。当局一旦开始犯错,并坚持下去,剩下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6月5日上午9时左右,一伙歹徒从东、南两个方向,用石头猛击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将二、三、四楼临街办公室窗户的大部分玻璃砸烂。随后,这些歹徒手持钢钎,木棒,冲开东面铁门,打砸停在院内的汽车,并放火烧毁了三辆轿车。下午,一些歹徒又聚集在市人大常委会门前,向办公楼抛甩汽油燃烧瓶,将行政楼引燃,这些人还猛撞围墙,企图冲进办公区,未逞。他们便在办公楼下叫骂:楼上的人下来,把你们全部杀死…
6月5日,从下午到晚上,一伙歹徒围聚在市政府办公大院东墙外左侧,对着正在进行广播的房间高呼:杀死所有的共产党员,杀死所有的公安!”
“6月5日,歹徒的暴行达到顶峰,他们倾巢出动,四面袭击,打砸警车,殴打武警、公安干警和解放军。从6月5日至6日,成都市区所有十字路口皆无交警上岗,街上亦不见穿警服、军服的军警人员。一些军警人员的家庭受到威胁,歹徒们叫嚣:先打警察,再打警察家属…歹徒们还闯进一、二、三、六等医院,搜寻受伤的武警战士,扬言‘搜出一个,就打死一个’。蜀都大道和一环路等地,每个交通路口都聚集着几百名歹徒。他们见军车、警车、轿车就砸,见军人、民警就打。他们喊着:‘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无冤无仇,就打欺头!’”(《成都骚乱事件始末》)
而武装斗争的主力,已经从学生转移到了长期受警察欺压的群众,这一点,共产党的材料其实比西方人看到的更清楚:
“石头、砖块、玻璃瓶如雨点般向人民东路派出所袭击。手持匕首,钢钎,大刀,木棒,铁棍的歹徒,声嘶力竭的对着人东派出所嚎叫着:
警察,黑xx!今天老子们要把你们黑xx锤平!
黑xx警察!你们整老子,你们晓得有今天的下场哇。老子要点一把火,烧!
宋良志(人东派出所所长)!你xxx是对的就出来!人东(派出所)的,还有戴大盘盘(帽)的,是对的都出来!老子们今天统统的杀死!
共产党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打!烧!冲哇!”(《歹徒们为什么要烧人东派出所》)
当然,和中国的材料想要宣传的相反,抗议群众其实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武器,装备和经验不足的局面。从西方和共产党的记录我们都可以看出,抗议群众的武器非常简陋,最有效的也只有燃烧瓶和高压气枪(只有共产党的记录,西方记录里并未出现高压气枪)。面对全副武装的武警和解放军,抗议群众很快失去了气势。从共产党的材料里来看,抗议群众分成许多个小团体,彼此之间并没有足够的支持,而武警一次的出动数量居然可以达到800名!6月6日,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抛弃了部分由他煽动起来的学生和抗议,给武警下达了镇压的命令,武警开始放开手脚,血腥镇压抗议群众。在武器,装备,组织和经验全面领先的武警面前,抗议市民仅凭人数优势无法获胜,被分割开来,各个击破:
我问他,既然民众是多数,为什么不将警察制服。
“在成都,这是新事物。我们没有这样的战斗的经验。人们很害怕。但我们不能再忍受了,所以我们加入了。如果警察向人们开枪,他们就会变得更勇敢,并去战斗。我们医学院/医院的院长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参与学生示威,就会受到惩罚。这是真的。他们在布告栏上贴了通知。”(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武警在抓捕学生和抗议者期间,对他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杀害:
“我回到我之前待着观望事态的那间房间的阳台上。不久,有六辆卡车载着看起来像是士兵的人进入大院。他们没有持枪,但似乎有类似刺刀的武器。他们与我过去两天见过的武装警察不一样。有一个人非常醒目。他穿着不同的制服,有一把套在枪套里的手枪。
这些士兵跳出来,见一个抓一个。真是一片混乱。大多数示威者、袭击者和围观的人都跑了出去,但大约有三十多人被抓,不管他们是破坏了财产还是只是看热闹的,士兵们不知道也不关心。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惊恐地看到这些士兵们殴打、虐待被捕的人。他们要每一个人向前迈出一步,双手绑在身后。他们给他们拍了照片,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头朝下扔到水泥地的停车场。他们的头骨脑袋撞到地面发出的嘭嘭声,令人毛骨悚然。
我受不了了。我跑到酒店的大堂,那里全是碎玻璃,被砸得稀巴烂。我发现士兵的领导正和其他的士兵站在周围。我走到他面前,开始用英语对他喊:“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是在没有任何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人。”我也不确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我不会说普通话,而他不会说英语。很快,一些警卫把我赶走了,我又回到了阳台,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
在他们“处理”完所有新的被捕者之后,士兵们又将他们扔到他们开来的其中一辆大卡车上,就像他们是一袋袋土豆。 如果那时那些人还没有死,那么压在下面的人很可能会窒息而死。凌晨3点刚过,他们就把车开走了。我不知道他们当中死了多少人。”(小天安门:美国议员回忆成都“六四”/纽约时报中文网)
“她看到了大约二十五个人跪在院子里,头朝下,双手绑在背后。他们先是被推到在地,然后卫兵围着他们走来走去将近一个多小时。最后,指令下来了。这时‘穿黑裤子白衬衫的人上来用铁棍把那些人的脑袋敲碎’。景象惨绝人寰,她吓得在浴室里呕吐。几天后,她逃离了中国。后来她告诉一家北欧的报纸,‘他们一个人一个人的杀,那些还活着的人不断哀求他们给一条生路。’”(《人民失忆共和国》)
惨烈的三日巷战,以巴蜀人民的失败而结束。
望帝有魂归不得,蜀山留住杜鹃声:民主运动失败以后的巴蜀
虽然当年的巴蜀民主化运动还仍然有许多没有能完全解释清楚的细节,有些细节也许将永远无法解释清楚,但我们已经可以从现有的资料里看出当年的抗议大体上是怎么回事:以成都为核心的巴蜀1989年的民主化运动并不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而是巴蜀人反抗中国政府和中国暴政的一次尝试。它跟历史上,尤其是红色中国统治下巴蜀的多次反抗更为类似。它也不是“屠杀”,而是以大学生的抗议为开端,以被红色殖民体系压抑的群众为核心的,跟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武警部队进行的长达三日的血战。它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抗议群众武器装备,军事组织和训练的不足。然而根本原因,来自于它缺乏真正有效的动员机制。正如运动一开始人们注意到的那样,大部分人并不是对抽象的“民主”,“自由”这些概念感兴趣的。更能动员他们的,反而是“复仇”,“抗暴”这样更简单朴素的情感。廖亦武先生在《子弹鸦片》一书中记录过一个四川广安籍的民运人士雷凤云,雷的故事最能说明当时真正的群众动力在什么地方:他说雷听到邓小平下令屠杀学生以后非常气愤,决心回去挖了邓小平的祖坟,雷凤云是这么说的:“在我们四川,如果某人造下天怒人怨的恶行,人们往往就挖他祖坟以示惩戒。” 当时运动的领袖们并未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因此遭到失败。然而这次运动的失败刺激了巴蜀的本土意识,廖亦武因此直接喊出了“这个帝国必须解体”,刘仲敬,笔者和许多巴蜀独立运动的参与者也正是在意识到“中国民主运动”不可行以后,才转而支持和参与巴蜀独立运动。接下来的故事,需要我们自己来书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