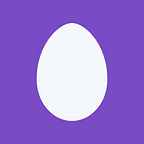東亞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 — 武昌起義前的軍事與財政體制的演變
前言:
辛亥年(1911)的獨立戰爭是了解東亞近現代史的鑰匙,只要能正確理解辛亥獨立戰爭,就可以對東亞的近代史和今天的格局掌握個大概。儘管或正因為如此,辛亥獨立戰爭才受到了非常嚴重的歪曲解釋。通常的解釋是兩種,一種是由中國國民黨發明的大中華主義敘事,這種敘事認為辛亥獨立戰爭是辛亥年間發生的革命,旨在推翻滿族人對漢族人的殖民統治,建立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共和國。一種是由中國共產黨發明的階級鬥爭敘事,這種敘事同樣認為這是辛亥年間發生的革命,是進步開明的資產階級對封建皇權的革命。從各個角度攻擊這兩種敘事的研究已經非常多了,但為了引出本文對辛亥獨立戰爭的重新建構,這裡仍然有必要對上述兩種敘事,從筆者的角度進行解構:
上述兩種敘事儘管有細節上的差別,但都可以被稱為革命敘事,也就是說,兩種敘事都認為辛亥獨立戰爭是一種革命,而且是一種社會革命。為了將就這種革命敘事,它們只好忽略大部分無法解釋的史實。比如它們解釋不了為什麼楊度可以從帝制餘孽搖身一變,成為共產黨員。它們同樣解釋不了為什麼汪兆銘要“一生分作兩回人”。它們的解釋力匱乏的主要原因是,辛亥獨立戰爭所代表的根本就不是社會革命,換句話說,辛亥年間的戰爭所追求的根本就不是“消滅帝制”,“民主自由現代化”,或“階級鬥爭”,而是從太平天國以來的各種歷史可能性,因為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這兩個偶然事件,在辛亥年突然以爆炸性的方式展開。這些可能性有:以清帝的合法性為基礎的君主立憲,以建立新中華帝國為目標的帝國重構計畫,以關內關外為分界線的東亞-中亞分治,以各省自治為核心的東亞聯邦,以各省獨立為訴求的東亞多國體系。很明顯,這些可能性並不是完全互斥的,它們互相之間有許多共通的路線,因此,我們才可以解釋為什麼楊度,汪兆銘還有許多同時代的人會做出各種各樣今天的人看來是非常令人驚訝的路線選擇,這不過是因為他們在共通的路線上走到了路口,然後轉向不同的岔路而已。然而正是這種豐富的歷史可能性才是東亞自由和繁榮的基礎,本文因此希望通過重構從太平天國到辛亥年間的歷史,來說明辛亥獨立戰爭并不是“革命”,而是辛亥前夜的各種可能性在東亞不同的地區展現,進而證明中國或中華帝國以前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會是東亞的唯一選擇。
清帝國崛起與東北亞,逐漸征服了東亞,中亞東部和東南亞北部的廣袤土地。大清皇帝是滿洲,蒙古和圖博的共主和領袖,是其餘地區的征服者。征服者建立的帝國要維持在被征服地的統治,可以設計各種符號和五花八門的形式,但核心無外乎兩項:財政與軍事。有了這兩項,帝國尚存,沒有這兩項,帝國滅亡。因此,清帝國在東亞和東南亞的崩潰其實始於川楚白蓮教之亂,終於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前者破壞了帝國的財政結構,後者摧毀了八旗的軍事建制。川楚白蓮教之亂打空了國庫,暴露了帝國僵硬的財政體系無法鎮壓揚子江以南的山地(學術上所謂的贊米亞地區)對帝國的抵抗,開啓了名為鄉勇的潘多拉魔盒。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消耗了帝國的精銳。八里橋之戰打光了清帝國最精銳的騎兵,揚子江以北的捻軍自此在馬背上難逢對手,僧格林沁的陣亡為滿蒙舊騎兵的滅亡畫上了一個句號。至此,清帝國自征服東亞和東南亞以來的軍事財政體制完全崩潰,被征服地的自發秩序開始茁壯成長。揚子江以南的各共同體有自發秩序,卻缺乏更高級的政治型態來保護;滿蒙擁有帝國,卻菁華喪盡,需要時間重組共同體;西方列強無意直接介入,願意跟大清皇室進行交涉,三方因此妥協,共同經營,才有所謂的同治中興,然而中興以後的清帝國,已經不是康乾時期那個由征服者建立起來的清帝國了,它是各方政治勢力妥協的一個代理和中間機構。苟且之治當然無法長期維持,因此各方勢力開始了博弈和鬥爭,從中產生出了前述的各種歷史可能性。而這一切都是清帝國的舊制度因爲無法應付太平天國造成的動亂而引起的,東亞的近代史從天平天國開始,即因爲此。
太平天國源於在清帝國體制中被壓抑的南粵、桂蘭社會。清帝國本質上作爲東北亞帝國,和與南洋有諸多聯係的南粵社會無法兼容。晉商是朝廷的親支近派,被大量派往南粵擠壓本土商人的勢力。南粵儒學和科舉不興,無法產生自己在朝廷的代理人;地方宗教興盛,與外界交流頻繁,以至於更容易獲得外來的宗教和秩序的輸入。洪秀全以科舉落榜生一轉而為基督教與巫術雜糅的“拜上帝教”的領袖,可謂頗有象徵意義。太平軍的兵源來自於在清帝國中找不到出路的南粵、桂尼士蘭人。清帝國稱呼太平天國為“粵匪”,進一步刺激了南粵和桂蘭的共同體意識。康有爲在面見清德宗以前,將大清國稱“大濁囯”,並揚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孫文則一直把洪楊當成自己的前輩和榜樣。所謂的“滿漢矛盾”,其實歸根結底就是滿粵矛盾。太平天國的覆滅沒有對南粵社會傷筋動骨,他們在等待一個再起的時機。
舊軍事和財政體制的崩潰瓦解了舊帝國。新的軍事和財政體制的產生也孕育了新的政治共同體,以湘軍為代表。湘軍以贊米亞地區常見的山地共同體的組織度為底色,以儒家學説為理論資源,以“辦團練”和“自行籌款”的政策為經營對象,以“自强”和“洋務”為技術輸入渠道,最先在東亞形成了民族國家的雛形。湖湘地緣形勢險惡,强敵環繞,又遠離西方帝國主義的蔭蔽,能夠成爲東亞強藩長達半個多世紀,主要就是因爲湘軍的政治共同體在戰爭的刺激下,形成得最早,最完善。湖湘的地主與土豪承擔軍費,其中的佼佼者既向清帝國爭取更好的政策,又向西方爭取技術和資金。地主與土豪們的子孫擔任軍官,平民擔任士兵,既可以維持鄉土秩序不受戰爭和中央暴政的侵害,又可以在有餘力的時候輸出武力和秩序到其他地方。以後東亞的大多政治共同體,都有意無意的在模仿這種“軍權保護財權,財權鞏固政權”的結構。
這裏需要額外補充一點。在東突,陝西,昭武和滇囯的穆斯林社區中產生出了在共同體組成的結構和理論資源上不同於湘軍的政治共同體,這是由中亞的穆斯林秩序輸入產生的餘波。中亞穆斯林社區保護了基層共同體,因此他們才有可能在天下大亂的時候形成一系列武裝政權,而所謂的“囘亂”,其實就是同治年間因清帝國勢力崩潰而自發產生的保境安民的小政權。清帝國處理“囘亂”的方法其實就是“以夷治夷”,比如用桂人岑毓英(岑春煊之父)打擊滇人杜文秀,或用湘軍進駐東突。其實質是給一部分有戰鬥力和組織力的共同體予政策,資源和大義名分,來打擊另外一批同樣戰鬥力和組織力很强,但對帝國有威脅的共同體。湘軍是其中最親近清帝國的勢力,因此受到重用。
當然,清帝國無法真正信任湘人,沿用中華帝國限制強藩的技術,一方面重用湘軍,對湘軍將領高官厚祿,在具體政策上對湘軍和湖湘人大量讓步,另一方面,也將曾國藩和湘軍領袖們調離鄉土,讓他們東征西討。湘軍士兵在隨軍征戰東亞各地的過程中,逐漸被腐蝕,有抛棄鄉土,去江南揮霍和發橫財的跡象出現,毛澤東的父親毛貽昌就是這種兵痞。物質財富的積纍無法彌補共同體組織度的損失,曾國藩憂心忡忡,因此萌生退念。在他的世界裏,他并不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他只是延續了羅澤南和胡林翼的未竟之業,希望保境安民而已。
與此同時,江淮人李鴻章野心勃勃,正在組建淮軍。江淮社會介於湖湘和吳越之間。論文,江淮不如吳越,論武,江淮不如湖湘,淮人急需一個更明確清晰的定位來拓張自己的勢力。與此同時,江淮又是湘軍和太平軍交戰的主戰場,他們對備戰的需求也更爲迫切,因此產生了東亞罕見的偉大外交家李鴻章。他這一生,主要就是在各方勢力之間周旋的同時,為江淮社會和淮軍領袖贏得利益。淮南在太平軍的掌握之中,淮北又經常受到捻軍的騷擾,李鴻章的淮勇五營的兵源因此主要集中在合肥一帶。外交是以權力為本錢的金融游戲,李鴻章的本錢就是這淮勇五營。他依靠這五營來撬動權力的杠桿,加上從湘軍借調和從蘇北招募的吳兵,搭好了淮軍的架子。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淮軍一開始就跟湘軍不一樣。湘軍仍然是本地武裝,是湘人依靠鄉土共同體組建的軍隊。而淮軍的主力和核心雖然是合肥一帶產生的軍官和士兵,但軍隊的組成已經有了大量的外地士兵。因此淮軍不能指望鄉土共同體的自發秩序作爲凝聚軍隊的紐帶,而一來必須依靠李鴻章個人超高的協調技術,二來必須再次依靠李鴻章過人的外交手腕,從清帝國和西方那裏得到資金,技術和武器。因此李鴻章在淮軍中的權力比曾國藩在湘軍中的權力要大得多。而又因爲淮軍的鄉土性比湘軍弱了不少,所以他們更愿意作爲清帝國的雇傭兵南征北戰,從剿滅捻軍開始,到1875年進攻台灣,1884 年與法囯在越南交戰,1894年與日本在朝鮮和海上作戰,淮軍越來越像一隻帝國軍隊,而不是淮人的軍隊。它介於湘軍和帝國新軍之間,仿佛江淮介於湖湘和中國之間,李鴻章介於曾國藩和袁世凱之間。總之,天平天國雖然沒有立刻解體清帝國,卻徹底的改變了清帝國作爲征服者的性質,讓帝國不得不解放贊米亞地區的各邦,允許它們武裝自身,這為後來各邦的獨立鋪好了路。
同治中興帶來的三十年和平只是相對而言,小規模的地方衝突和境外戰爭一直在發生。從清帝國的角度來説,自强運動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大清的國力有所增强,但滿蒙親貴的地位在帝國内部卻進一步下降了。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依靠經營洋務政策,獲利頗豐,更爲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向外建立了與洋人交流的渠道,對内建立起了自己的勢力範圍,長此以往,帝國終將分裂。孝欽后先後用左宗棠,翁同和,張之洞等人來鉗制李鴻章,也只是按下葫蘆起了瓢。不談湘軍出身的左宗棠本身就不可能比李鴻章對清帝國更忠誠,哪怕是對帝國最友好的吳越人翁同和和幽燕人張之洞,也撥打著自己的小算盤。翁是帝師,時刻都想恢復德宗的憲法權利,張是新中華帝國的主要策劃人,主張化除“滿漢畛域”,建立滿漢聯合帝國。很明顯,哪一個都不能讓西太后真正滿意。
自强運動時期真正的鬥爭來自於路綫鬥爭,軍事財政體制既然無法恢復到太平天國以前,那麽道咸時代的意識形態自然就只能過時。倭文端公説的一句話都沒有錯,可是已經沒有人可能聼他的話了。洋務派的路綫如果走到底,就是“東南互保”式的東亞聯邦。張之洞的路綫如果走到底,就是《十九信條》裏設想的那種君主立憲。淮軍尾大不掉,洋務卓有成效,清帝國除了放任這兩條路綫繼續發展以外,也沒有更多的辦法。清廷可以打擊個人,卻動不了整個機制。張之洞在此期間對兩地下過最大的心血,後來這兩地最先爆發了辛亥獨立戰爭 — — 即巴蜀的保路運動和荊楚的武昌起義。
巴蜀此時的元氣已經從張獻忠屠蜀后恢復,在藍大順和石達開的刺激之下開始有一些小規模的地方武裝。其中最優秀的武裝來自於高蜀,也就是成都平原以外,四周的山地產生的袍哥和商團組織。湘軍名將鮑超,就來自於夔州,他的“霆字營”裏,就包含了大量的巴楚邊境的袍哥,“蜀勇則哥老甚多”。因此,與曾國藩和李鴻章這種畢竟士大夫出身的人不同,鮑超這個大字不識一個的人以江湖和會黨為組織凝結核。藍大順入蜀南,刺激了巴蜀地主的團練和巴蜀鹽工的武裝化。但由於巴蜀地域遼闊,而且受到的戰爭壓力遠不如湘,淮,粵,因此沒有產生出足夠强大的政治共同體。跟湘粵類似,巴蜀的儒風也不盛,然而張之洞到來以後,情況爲之一變。張之洞根據他自己的理想,培養了大量的巴蜀籍君憲主義者,他們中的大多數,後來在多次政治運動中與巴蜀父老和人民合流,反而成了對抗新中華帝國的中堅。
荊楚是東亞的交通樞紐,太平天國時期自然成了湘軍與太平軍鬥爭的主戰場之一。湘軍後來逐漸獲得優勢,荊楚的地方武裝和團練因此直接複製于湘軍。太平軍切斷海鹽,使得蜀鹽得以銷往荊楚和其他地方,既促進了巴蜀商團的武裝和現代化,也使蜀楚的交往日益密切。如果張之洞對巴蜀的經營還只停留在學界的層面,他在荊楚的經營就是全方位的。實業,教育,軍隊,基礎建設,張之洞傾盡全力。漢口則是通商以來内地最國際化的地方,荊楚以漢口為核心,大量輸入西方的金融,軍事和工業體系。鄂軍後來以一省之力足以跟北洋軍抗衡,就是因爲有漢口這個國際大都市的緣故。然而荊楚跟巴蜀一樣,地方認同弱於湘粵,因此無法使出全力,但已經具備了可以威脅清帝國的實力。
甲午是自强運動這個苟且時期積纍的各方矛盾的縂爆發。帝后同心,表示大清已經自强了這麽多年了,現在兵強馬壯,國力强盛,應該抖一抖威風了。這句話的潛臺詞是,大清花了這麽多錢,犧牲了這麽多原則,打造了一支强大的海軍,建立了一套讓我們并不是很舒服的體系,忍辱負重這麽多年,該揚眉吐氣了。這不光是朝廷的想法,曾紀澤用英文寫成的《中國先睡后醒論》,持同樣的看法。他認爲他在伊犁和其他地方的外交成果足以彰顯國威了,大清已經强大,是時候收回她對各屬國的宗主權了。只有李鴻章明白内情。錢,太少了。不是大清的國内生產總值太少了,而是可以供他支配的資金太少了。清帝國的財政結構處於混亂的狀態,清廷不知道各省督撫到底有多少錢,翁同和利用北京對李鴻章的猜忌,處處掣肘。“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可謂精確的描述了督撫與清廷的互相猜忌,各部門,各督撫當然就只好自己給自己留一點自留地,因此,雖然在西化的大背景下收入一直在增加,但具體到各個需要用錢的點,尤其是非常花錢的購買武器裝備和訓練軍官士兵,反而更加不夠,而軍費開支只會越來越多。李鴻章的交涉技術在甲午前夜越來越像龐氏騙局,因爲他解決不了北洋海軍缺乏軍費而打不了仗的問題,正如龐氏騙局解決不了空殼公司無法擁有真實項目的問題。
甲午戰敗,淮軍集團作爲有影響力的政治集團倒臺,留下了大量的權力和職位真空。雖然有許多淮軍將領投靠了袁世凱,但江淮社會繼續成長,才可以在辛亥年閒產生柏文蔚和孫毓筠。清帝國認爲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南方人終究不可信,南方人認爲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們的權力還不夠大,李鴻章和洋務派打造的緩衝地帶隨著合肥本人的倒臺而消失,雙方的衝突馬上就要爆發。戊戌變法的實質,是南方士大夫與年輕氣盛的皇帝的結盟,試圖拓展各省的自主權。對外,士大夫想要借用“立憲”的名義,替代李鴻章和淮軍的地位。年輕的德宗也深感被太后壓制,渴望大展拳脚。所謂的“戊戌六君子”,其實并不是同一批人。楊銳和劉光第來自巴蜀,是張之洞留下的君憲主義者中的佼佼者,他們感到巴蜀已經足夠强大,可以為自己在帝國内贏得更大的地位。譚嗣同是湖湘社會產生的精華,認爲湖湘的東亞“斯巴達”地位早該通過立憲而得到認可。與他們相比,康有為和梁啓超的影響力仍然只停留在輿論和外圍的層面。然而對滿蒙親貴而言,比起聽話的中國主義者來説,他們的忠誠太有問題了,比起李鴻章來説,他們又太好對付了,因此實力對比的懸殊讓維新黨人輕而易舉被擊敗,由此產生了三個後果:1.部分維新黨人開始朝革命黨人轉向;2.中華帝國主義者的代表袁世凱擡頭;3.由庚子引發的東南互保。第一個後果已經有很多人提到了。第二個後果讓張之洞設計的新中華帝國在袁世凱身上看到了實現的可能。袁世凱出身淮軍,生涯早期借用帝國的名義為私人謀地盤,不管是在小站還是朝鮮,在此時還屬於積攢實力的階段,但已經有了不臣之心。第三個後果是將南方各省與清廷的矛盾公開化,地方勢力第一次嘗到了獨立的滋味。
滿洲的民族主義幾乎與“漢人”的民族主義發源於同時,基於滿洲人不願意受被征服者統治的情感。從南方的滿城裏查抄出的東西來看,儘管南方的旗人在各方面已經跟他們駐地的“漢人”區別不大,卻仍然執著的要在符號性的東西上堅持滿人的傳統。這種堅持雖然不能讓他們重回順治年間的戰鬥力,卻仍然可以成爲滿洲民族復興的情感助力。庚子以後,滿蒙親貴奪回了跟西方交流的渠道,因此產生了一大批親貴軍官,尤其重要的是禁衛軍的軍官,比如良弼。後來抵抗革命黨人最堅決的,也大都來自禁衛軍。然而這時候,滿洲人想要再以親貴為核心奪回帝國的統治機器已經非常困難了。一方面是以袁世凱為代表的中華帝國主義者,不希望親貴再次上臺,另一方面是南方的地方派也已經佔據了相當大的地盤。陳寅恪所謂“養兵成賊”的格局,在新軍尚未建立起來就已經露了出來。但爲了維持帝國的門面,這隻危險的新軍,仍然不得不練。在地方勢力強的省份,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對清帝國頗有不滿。在中國本部,袁世凱的地位無可動搖。袁世凱這時有沒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仍然不清楚,張之洞力保袁世凱,或許就是發現不能太刺激他。他在病床上聽到攝政王載灃居然認爲新軍可靠,吐血而死,可謂是為帝國盡忠到底了。攝政王都如此,張之洞已經預見到了帝國的解體,剩下的只是如何解體的問題了。
清帝國和中華帝國主義者合作的點在於集中權力,但只要是任何集權項目,都有可能觸動地方派敏感的神經。公平的說,川漢鐵路公司裏一定有很多見不得人的帳。跟川漢鐵路關係不大的蜀籍京官,比如宋育仁和甘大璋,完全不反對國有化。而其餘巴蜀士紳如此激烈的反對國有化,到底有幾分是出於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也許將永遠無法知道。但這一定被不少人感覺到了,因爲至少像李劼人這樣的人,在《大波》裏,也做出了相當明確的暗示。然而這些根本就不是問題的關鍵。巴蜀士紳利用所有巴蜀人都是鐵路公司的股東這個先天的優勢,將保路與保川合二爲一,煽動了巴蜀人的本土意識。“四川人”的政治發明也成爲了立憲黨人和革命黨人可以合作的基礎。而荊楚的革命黨人就比巴蜀的要强大得多,主要原因是荊楚受到西方的秩序輸入更多,獲得新思想,新武器和新情報的機會更多,所以可以獨自發動兵變。這就來到了武昌起義的前夜。
武昌起義以前各歷史可能性演化表:
川楚白蓮教之亂摧毀了清帝國的財政體制,逼迫清帝國實施“鄉勇”,讓各省可以自己組織武裝,但舊的軍事體制還可以勉强維持。太平天國徹底瓦解了清帝國的軍事和財政體制,解放了東亞各地的枷鎖。
結果:以清帝為合法君主的君主立憲體制可能性最大,以東亞-中亞為界限的分治可能性較小,其他可能性還微不足道。
自强運動時期讓各省督撫有了更大的權力,西方思想的輸入讓他們開始逐漸發展出新的理論支持他們的事實權力,不必拘泥於對清室忠誠。同時,淮軍開始發展出了想要盤下帝國的苗頭,清帝國在各勢力之間追求平衡,希望維持滿蒙親貴的特殊地位。
結果:君主立憲可能性下降,新中華帝國、東亞聯邦和各省分開獨立的可能性開始出現。
甲午戰敗,君憲主義開始提上日程,成爲主流。但君憲主義開始各表:親貴中的一部分和中華帝國主義者要求建立新帝國,實力督撫要求擴大地方自主權,雙方撞車與戊戌變法和庚子事變。南方實力派先輸后贏,在東南互保以後已經具備了獨立的所有條件。
結果:君憲的可能性繼續下降,東亞聯邦可能性大增。同時,革命黨開始產生,東亞-中亞分治的可能性小幅度上升。袁世凱崛起,接替淮軍生態位,張之洞《勸學篇》發表,新中華帝國的可能性也小幅度上升。
庚子以後,清帝國奪回與西方的交流渠道,親貴受到優秀的訓練。民族主義興起,滿“漢”矛盾更深。地方督撫也開始派出留學生。袁世凱受到打壓,張之洞病逝。
結果:君憲可能性降至最低,東亞聯邦可能性基本維持不變,各省獨立可能性小幅度上升,東亞-中亞分治可能性大幅度上漲,新中華帝國可能性小幅度下跌。
蜀紳保路,楚黨起義。各種可能性開始碰撞。君憲主義率先出局。袁世凱的新中華帝國受到革命黨,宗社黨和地方實力派的三重壓制,退居幕後,直到他試圖稱帝時期才被徹底打垮。革命黨與實力派合流,并在西方的斡旋之下,滿足於事實上的東亞-中亞分治。東亞部分,聯邦與各省獨立的矛盾開始慢慢醖釀,在共同的敵人,新中華帝國主義的代表袁世凱被消滅以後開始爆發,在1920年代初開始往有利於各省獨立的方向發展,直到被蘇聯控制的國民黨和共產黨聯手打破。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裏所展示的那樣 — — “革命”只是表象,舊制度不僅沒有被革命修改,反而在革命后進一步發展 — — 東亞也是同理。“辛亥革命”並沒有打破太平天國以來,趨勢向各地獨立發展的格局,反而促進了這個趨勢的發展。沒有蘇聯的干涉,東亞的多國體系可能早在一百年以前就成型了。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小概率事件的結果,而我們今天所認爲的小概率事件,即中亞,東亞和東南亞各邦獨立,卻曾是一個大概率事件。舊制度的瓦解在東亞,總是會解放出多國體系的可能性,只要恢復了這個可能性,歷史的進程仍在我們自己手裏。這當然也意味著,我們既沒有必要絕望的認爲東亞已經沒救,也不能樂觀的認爲必將到來的解體總會自動帶來自由,每個個體在此時的選擇都會對這個世界的發展產生影響,這是爲數不多的個人選擇可以影響歷史的時期,請各位不要辜負歷史的機遇。